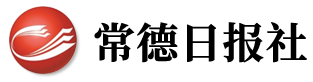“4·20”雅安地震采访手记
4月20日至30日,三次从常德出发,三次从雅安归来,最大的感概是,我想我算是过了媒体生涯的“见习期”。
记得初入报社时,一位老记者说过,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自身,想要修好行至少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磨几年,因为记者这个行业靠的是阅历,什么都无法替代。”三进庐山地震重灾区,10天10夜,近8000公里路程,脚踏实地经历了地震灾难,亲眼目睹了人间悲剧,让我了对记者这份职业倍加珍惜和更深的思考。
不深入不能了解全面真相
4月22日上午,国内某卫视及官方微博播发了一则“宝兴县灵关镇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”的消息。在大灾大难时期,这样的讯息在新闻记者看来,确实是一则猛料。按照先前的计划,我们的第一批爱心物资将运往灵关镇,“到时候我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消息是否属实”,一路前进中,我内心这样盘算着。
由于前往宝兴的路遭遇滑坡中断,我们临时决定前往芦山县。下午6时许,我们经过芦山县重城郊时,正好碰到几户灾民正在倒塌的房屋前做晚饭,我决定下车看看他们有没有“大鱼大肉”。一锅油汤还没煮开,灾民说,他们全家的晚餐就是水煮蚕豆。上车继续前进,不到百米的距离,在一片帐篷前堆,一名妇女正在宰杀一只大母鸡。我终于“逮到了证据”,当即拍了照片,准备发微博时又放弃了,但内心却不是滋味。
23日上午,在当地志愿者罗径的帮助下,爱心物资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。休息中,我把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,话刚落音,罗径便哈哈大笑起来。“你误会啦,宰鸡的灾民肯定是为了救人,那只鸡可能救了上百人哦”罗径说,地震当天正好她母亲的82岁生日,因为小区的房子几乎全倒了,到了晚上,小区里一天滴水未进的老人小孩都饿倒了,他老公冲进家里,将炖好的鸡肉和米饭抢出来,熬了一满锅鸡汤粥,让小区里80多名老人和小孩在地震后第一晚垫了肚子。当天下午返回时,在210省道遇到了从宝兴县前往雅安市区的灾民冯军,交谈中说起了“宝兴县灵关镇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”的事。“谣言、都是谣言hellip;hellip;”冯军介绍,中坝村村民舒正山建新房后宴请亲朋好友,20日凌晨4点多,他家杀猪准备宴席。8点02分,刚刚杀完5头猪,地震突然来袭,舒正山家是新房,受灾不太严重,他在地震当天下午就将杀完的5头猪煮熟,切块分发给周边村民。晚上我从新闻证实了冯军的说法。心中的疑惑全部解开。我深知故意传递不实信息、制造混乱,乃新闻之大忌。为了追求新闻轰动效应不惜为之,更将丧失了一个记者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职业素养。只有采访越深入,才能了解全面认识事物的真实状况。
不要揭开采访对象滴血的伤口
第一次前往芦山时,志愿者罗径给我讲述了她朋友陆静康的故事。陆静康的儿子在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遇难,17岁的女儿又在这次地震中被自家垮塌的房屋压死。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,罗径说可以带我去采访陆静康,最终因为时间紧张未成行。在回常德后,国内的多家媒体道了陆静康的故事,50岁的陆静康被誉为悲情母亲。
4月25日,第二次前往芦山,我们又找到了志愿者罗径带队,在城郊经过一座废墟时,罗径说这就是陆静康的家。我当即下车,在屋前的帐篷边上,有几个记者围着一个头发蓬乱、浑身褴褛的女人,一边讲述一边痛哭。站在人群外围,我听陆静康介绍,她的女儿岳宇珊是个“最最乖巧懂事的女子”、“她学习好,是年级第14名”、“她正在读高二,马上就要高三了”、“她说要考上一个好大学,将来当英语老师”。记者继续追问岳宇珊被埋的情形,陆静康说,地震两个多小时后,武警从废墟中找到了她的女儿,“她还穿着背心和内裤,全身的土灰已看不清她的脸。没有流血,就像她哥哥一样,没有了呼吸,表情很平静,就像睡着了hellip;hellip;”陆静康话还没说完,就嚎啕大哭起来。“走吧。”我喊志愿者和罗径离开。“不采访了?这么好的新闻hellip;hellip;”他们十分不解。我继续离开,没有回头,也不说话。刚刚失去女儿,陆静康的伤痛不堪回首,而媒体又偏偏要挖掘这些细节来塑造、突出这位母亲的悲壮。在记者们充满热情和崇敬的多次采访中,陆静康反而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哪一颗饱受创伤的心能经得起这样的反复揉搓呢?当晚发放完爱心物资返回时,罗径准备去看看陆静康,我拒绝前往,我说,我不想让陆静康又一次揭开滴血的伤口,那样做,对她太残忍。
在当地一家成都吃晚饭时,餐馆的电视正在播放地震灾情连线节目,记者在一堆废墟前问两个女孩在地震时看到了什么,那两个女孩子泣不成声地描述遭遇地震时的情形。两个女孩本来从地震的惊恐中刚刚脱离,需要的是心理治疗,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哭着来叙述那些他们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情景?仅仅为了煽情吗?
我想到了一个对所有记者来说都非常难解的命题,面对痛苦的采访对象时,是保持职业习惯冷眼旁观,做一个专业的记录者,还是参与到救助过程中,满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立场?我很能理解一个前方记者面对一个珍贵的新闻线索时的兴奋,更重要的是还肩负了要让外界了解真相的责任感。只是我也怀疑,如果这样的真相必须是建立在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无情忽略时,那么它的存在或是客观性还有没有必要?当新闻采访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时,记者的行为是不是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。面对极端的场面,是伸出帮助的手,还是拿出摄像机?
发出微博后,没人给我答案。在整理自己的行程中,我发现我三进庐山地震重灾区后,我不是第一时间拿起照相机记录第一手的资料,而是每次都会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,投入了救灾的工作中,帮灾民搬送物资、搭建帐篷。